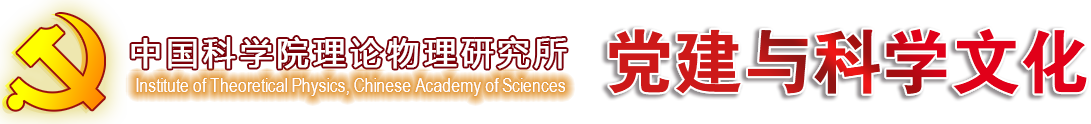大家风范
何汉新:忆彭桓武先生二、三事
来源:《物理》杂志
时间:2005-06-13
彭桓武先生是我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做大学毕业论文(1963。9—1964。6)的导师,也是我随后在原子能所做研究生时的导师。在彭先生从事科研工作70周年并迎来他90华诞之际,40年前有幸跟随彭先生学习的往事,像电影般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那段经历是我的一份财富。这里我只记述印象深刻的二、三事,向彭先生贺寿。
我的大学毕业论文是关于高压下物质的状态方程。研究内容涉及到量子力学、热力学与统计物理及固体物理方面的知识。当时我在中国科大近代物理系理论物理专业学了四大力学及原子核理论,但未学固体物理课程。彭先生给我指定了有关固体物理学方面的参考书,并告诉我要边做研究工作边学习。有一次,在讨论到在高压下原子在固体中的间距变小、对晶格排列的影响等问题时,我向彭先生提出了有关的问题。彭先生在对相关的问题作了一些的解答后,对我说,他对有些问题也理解得不清楚,要去请教黄昆先生。两天后,他特地到教室来告诉我关于他和黄昆先生讨论有关问题的结果。又一次,在探讨如何用统计力学模型描述高压下的状态方程时,我向彭先生提出了一些问题。彭先生在对问题作了一些分析、讨论后,告诉我,有些问题他要去请教王竹溪先生。
彭先生当时在国内已是知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在我们学生的心目中是一位理论物理全才。我当时还是未出校门,仅做过一些课堂习题而对研究工作一点不懂的学生。但彭先生在指导我们做毕业论文时从不摆出“理论权威”的姿态,而如上面的例子提到的那样,即使在学生面前,对待科学问题始终表现出“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的严谨态度。彭先生对待科学问题的严谨求实、虚心好学的科学态度和作风,对我以后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有深刻的影响。
彭先生当年指导中国科大近代物理系理论物理专业学生的毕业论文时,除了我外还有张锡珍、阎沐霖、丁五美等共6位同学。彭先生当时正值领导我国的核武器理论设计,工作十分繁忙。但彭先生基本上是每星期四下午到我们所在的教室来指导和解答问题,如果那天下午他因事不能来,则会通知我们改在晚上或改天再来。彭先生在指导我们毕业论文时,除了指导我们具体学术问题外,有很多时间则是向我们传授关于开展科学研究的思想、方法、技巧直至论述个人的科研工作与国家事业的关系。
彭先生在教室一一解答我们提出的疑问后,有好几次带着我们6位同学在中关村的马路上边走边海阔天空地谈他的治学之道。当年的中国科大近物系的高年级部设在中关村的一座小院里。那时的中关村范围较小,路上的车也不多,有两次我们绕着中关村转圈多次,直至晚上十点多钟。彭先生的谈话内容涉及学习与科研、理论与实践、继承与创新等问题,其中不少内容已在他后来写的短文中总结成文。这里我只记述给我印象很深的两次谈话。一次是彭先生提到朗道那套理论物理学教程。彭先生说,他看了朗道的“理论物理学教程”,感到那套书确实写得很好,朗道的学识很广也很深。正因为这样,朗道才能在理论物理的多个领域做出杰出的研究工作。他也提到朗道在遭遇车祸、失去不少记忆后重新从基础学起的坚强毅力和追求科学的精神 。另一次,彭先生对我们谈起个人的前途与国家事业的关系时说,他对他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指彭先生当时从事的核武器研制工作)感到无比自豪,是真正为国家做了点事,以前所发表的那些论文与之相比真有些微不足道。
回想起来,这两点不正是彭先生一生对祖国的事业和他在科学事业上不懈追求和献身的写照吗?
鼓励学生在科研中创新、不要受老师思想的束缚,这是彭先生指导学生的一个基本思想。彭先生在指导我们大学毕业论文时的第一堂课就指出,学生不要受老师的框框的束缚,有新的思想和解法等都可提出。彭先生在指导我和刘寄星、张锡珍做研究生时更是强调了这一点。当时张锡珍是彭先生指导的研究生,我和刘寄星是黄祖洽先生指导的研究生,我们的研究方向都是等离子体物理理论,实际上是彭先生和黄先生共同指导我们。彭先生和黄先生当年在九院忙于核武器理论设计工作,只是一个月一次到原子能所指导我们,有时只是他们中的一位来原子能所作指导。第一次与我们三位研究生见面、指导的是彭先生一人。当时,他谈到为什么要我们三位从事等离子体物理理论的原因,告诉我们一定要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锻炼成长,指出我们作研究生论文时不要受题目的限制,要大胆创新。彭先生以他带的第一位研究生(后来才知是指黄祖洽先生)做论文时提出自己的方法求解问题为例,鼓励我们要在选题、解题方法等方面敢于创新,提出自己的想法。说到创新问题,我也必须提及黄祖洽先生在指导我做研究生时的一次谈话。他指出,要做出好的工作必须要有创新。
在后来从事的科研工作中,我一直铭记着彭、黄二位先生关于科研中要开拓创新的教导。
纵观彭先生的科研道路——从早期在量子力学、介子场论领域的工作到核武器研制工作,直至后来开展理论物理与化学、生物学的交叉领域研究工作,彭先生的一生就是不懈地继承又开拓创新,而严谨求实始终贯穿其中。
由于众所周知的“文革”原因,彭先生和黄先生指导我们做研究生的工作在1966年下半年中断了。直至改革开放,彭先生领导的理论物理研究所成立和理论所开放课题设立后,我和彭先生又有了联系,并再次能受到他的指点和帮助。例如,在2001年10月我到理论所参加学术活动时遇到了彭先生,一见面他就问我的工作是否有新的进展。我告诉他,我导出了新的对称性关系——横向的Ward-Takahashi关系。他随即问:这关系有什么用处?彭先生的这一提问引起了我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的思考,从而逐渐形成了如何从对称性关系建立基本相互作用的非微扰形式并用于探讨禁闭等非微扰基本问题的研究课题。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四十多年前指导我们大学毕业论文时正值风华正茂的彭先生如今已年近九旬。我和刘寄星、张锡珍等几位晚辈在近几年节假日拜访我们这位敬佩的老师时,见到他仍是孜孜不倦地伏案推导、思考理论物理问题。见我们去了,他还是不时地关心我们每个人的工作,并阐述他对一些理论问题的看法,我们还是幸运地享受他的教导。彭先生真是生命不止,科研的脚步不停。在彭先生从事科研70周年、并即将迎来他90华诞之际,我衷心祝愿他科学研究青春永在,身体健康长寿!
我的大学毕业论文是关于高压下物质的状态方程。研究内容涉及到量子力学、热力学与统计物理及固体物理方面的知识。当时我在中国科大近代物理系理论物理专业学了四大力学及原子核理论,但未学固体物理课程。彭先生给我指定了有关固体物理学方面的参考书,并告诉我要边做研究工作边学习。有一次,在讨论到在高压下原子在固体中的间距变小、对晶格排列的影响等问题时,我向彭先生提出了有关的问题。彭先生在对相关的问题作了一些的解答后,对我说,他对有些问题也理解得不清楚,要去请教黄昆先生。两天后,他特地到教室来告诉我关于他和黄昆先生讨论有关问题的结果。又一次,在探讨如何用统计力学模型描述高压下的状态方程时,我向彭先生提出了一些问题。彭先生在对问题作了一些分析、讨论后,告诉我,有些问题他要去请教王竹溪先生。
彭先生当时在国内已是知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在我们学生的心目中是一位理论物理全才。我当时还是未出校门,仅做过一些课堂习题而对研究工作一点不懂的学生。但彭先生在指导我们做毕业论文时从不摆出“理论权威”的姿态,而如上面的例子提到的那样,即使在学生面前,对待科学问题始终表现出“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的严谨态度。彭先生对待科学问题的严谨求实、虚心好学的科学态度和作风,对我以后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有深刻的影响。
彭先生当年指导中国科大近代物理系理论物理专业学生的毕业论文时,除了我外还有张锡珍、阎沐霖、丁五美等共6位同学。彭先生当时正值领导我国的核武器理论设计,工作十分繁忙。但彭先生基本上是每星期四下午到我们所在的教室来指导和解答问题,如果那天下午他因事不能来,则会通知我们改在晚上或改天再来。彭先生在指导我们毕业论文时,除了指导我们具体学术问题外,有很多时间则是向我们传授关于开展科学研究的思想、方法、技巧直至论述个人的科研工作与国家事业的关系。
彭先生在教室一一解答我们提出的疑问后,有好几次带着我们6位同学在中关村的马路上边走边海阔天空地谈他的治学之道。当年的中国科大近物系的高年级部设在中关村的一座小院里。那时的中关村范围较小,路上的车也不多,有两次我们绕着中关村转圈多次,直至晚上十点多钟。彭先生的谈话内容涉及学习与科研、理论与实践、继承与创新等问题,其中不少内容已在他后来写的短文中总结成文。这里我只记述给我印象很深的两次谈话。一次是彭先生提到朗道那套理论物理学教程。彭先生说,他看了朗道的“理论物理学教程”,感到那套书确实写得很好,朗道的学识很广也很深。正因为这样,朗道才能在理论物理的多个领域做出杰出的研究工作。他也提到朗道在遭遇车祸、失去不少记忆后重新从基础学起的坚强毅力和追求科学的精神 。另一次,彭先生对我们谈起个人的前途与国家事业的关系时说,他对他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指彭先生当时从事的核武器研制工作)感到无比自豪,是真正为国家做了点事,以前所发表的那些论文与之相比真有些微不足道。
回想起来,这两点不正是彭先生一生对祖国的事业和他在科学事业上不懈追求和献身的写照吗?
鼓励学生在科研中创新、不要受老师思想的束缚,这是彭先生指导学生的一个基本思想。彭先生在指导我们大学毕业论文时的第一堂课就指出,学生不要受老师的框框的束缚,有新的思想和解法等都可提出。彭先生在指导我和刘寄星、张锡珍做研究生时更是强调了这一点。当时张锡珍是彭先生指导的研究生,我和刘寄星是黄祖洽先生指导的研究生,我们的研究方向都是等离子体物理理论,实际上是彭先生和黄先生共同指导我们。彭先生和黄先生当年在九院忙于核武器理论设计工作,只是一个月一次到原子能所指导我们,有时只是他们中的一位来原子能所作指导。第一次与我们三位研究生见面、指导的是彭先生一人。当时,他谈到为什么要我们三位从事等离子体物理理论的原因,告诉我们一定要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锻炼成长,指出我们作研究生论文时不要受题目的限制,要大胆创新。彭先生以他带的第一位研究生(后来才知是指黄祖洽先生)做论文时提出自己的方法求解问题为例,鼓励我们要在选题、解题方法等方面敢于创新,提出自己的想法。说到创新问题,我也必须提及黄祖洽先生在指导我做研究生时的一次谈话。他指出,要做出好的工作必须要有创新。
在后来从事的科研工作中,我一直铭记着彭、黄二位先生关于科研中要开拓创新的教导。
纵观彭先生的科研道路——从早期在量子力学、介子场论领域的工作到核武器研制工作,直至后来开展理论物理与化学、生物学的交叉领域研究工作,彭先生的一生就是不懈地继承又开拓创新,而严谨求实始终贯穿其中。
由于众所周知的“文革”原因,彭先生和黄先生指导我们做研究生的工作在1966年下半年中断了。直至改革开放,彭先生领导的理论物理研究所成立和理论所开放课题设立后,我和彭先生又有了联系,并再次能受到他的指点和帮助。例如,在2001年10月我到理论所参加学术活动时遇到了彭先生,一见面他就问我的工作是否有新的进展。我告诉他,我导出了新的对称性关系——横向的Ward-Takahashi关系。他随即问:这关系有什么用处?彭先生的这一提问引起了我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的思考,从而逐渐形成了如何从对称性关系建立基本相互作用的非微扰形式并用于探讨禁闭等非微扰基本问题的研究课题。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四十多年前指导我们大学毕业论文时正值风华正茂的彭先生如今已年近九旬。我和刘寄星、张锡珍等几位晚辈在近几年节假日拜访我们这位敬佩的老师时,见到他仍是孜孜不倦地伏案推导、思考理论物理问题。见我们去了,他还是不时地关心我们每个人的工作,并阐述他对一些理论问题的看法,我们还是幸运地享受他的教导。彭先生真是生命不止,科研的脚步不停。在彭先生从事科研70周年、并即将迎来他90华诞之际,我衷心祝愿他科学研究青春永在,身体健康长寿!
附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