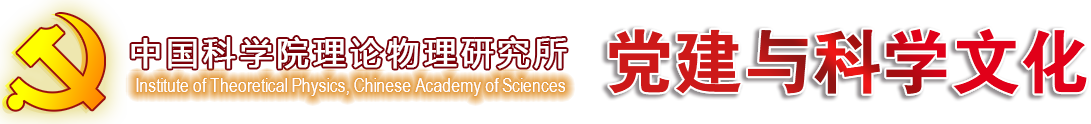大家风范
贺贤土:他把全部精力献给了祖国和物理学
来源:《物理》杂志
时间:2005-06-13
13与1之比,3就是无穷大
我于1962年11月底进入北京九所(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身)从事核武器物理研究。1963年初,进所后不久的一天,组长通知我们去听彭桓武先生给我们上的第一堂课。在大学学习时,老师就谈到彭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受人尊敬的理论物理学家,能听他讲课,感到十分荣幸。听课的人除了我们几位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和组内几位老同志外,还有我当时不认识的一位年长学者也来了。眼前的彭先生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个子不高、讲课声音较低、很随和、穿着朴素的一位“平凡”的科学家。彭先生讲课内容是关于随时间变化的γ射线点源在空气中的深穿透问题,需要研究多次散射、大能量慢化等过程,计算比较复杂。他的讲课不同于在学校时教师授课的方式,他一边讲γ射点穿透的难点,详细推导公式和具体计算,一边总是启发我们提问。由于我们在学校时习惯于听老师讲,比较胆怯,不敢提问题,但那位年长的学者(后来才知道是程开甲先生)则不断地向彭先生提问题和进行讨论,两人有时甚至争论得很剧烈。我感到这样讲课十分新奇,听讲时理解不深或似懂非懂的一些问题,经他们一讨论,感到明白了不少。我很感兴趣这样的讲课和听课方式。受了彭先生第一次讲课及后来几次讲课的启发,慢慢地我也学会在别人讲课和作报告时积极思考问题,大胆提问和发表自己意见,从中收益匪浅。
我与彭先生进一步接触是在1963年下半年,当时我从事了一项新的工作,研究由于外界突发因素的影响,在高超临界下系统还没达到设定的点火时刻以前,发生过早点火的概率,也就是研究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1964年上半年我们搬到新落成的14号楼办公,刚好与彭先生的办公室在同一层楼。由于我对彭先生讲课时的随和态度和讨论问题解答问题的作风印象很深,感到他没有大科学家架子,所以经常找他请教研究中遇到的问题。我所研究的方程是一个非线性积分微分方程,性质比较特殊,不同于一般的偏微分方程,自然无法求得精确解析解,需要作不同近似下的解。我对近似解是否可靠心里没底,常常找他讨论。他对这类特殊方程也很感兴趣,加上第一颗原子弹计划下半年试验,计算过早点火概率大小是一个重要问题,所以他对过早点火研究很关心。为了深入了解这个方程的基本性质,在他指点下,我从生成函数出发,仔细推导得到了有关中子与原子核各种相互作用的生成函数的方程,并在特定近似下获得了现在所用方程,写成了详细论文给他看。他看了很高兴,并指出了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我心里十分庆幸,参加工作后不久,就得到名师的指点。这个工作不到一年时间就完成了任务,并提供了物理模型由数学组的同志编成程序进行精确数值计算,为核试验提供了数据。他对这一工作一直很关心, 1970年代末他离开我们所时,还把他以前研究有关点火的稿子留下给我。
随着跟他接触增多,我发现彭先生有一个很大的本领,一个复杂的微分方程到他手里,他能很快估计出方程各项的相对大小,然后把小数的项去掉,保留大数项。在保留或舍弃一些项时,他形象地比喻为3与1之比,3就是无穷大,意思是1完全可忽略。经他这么一处理,一个复杂的微分方程就常常容易得到近似解,甚至变成一个特殊函数方程,解自然就出来了。当年的很多年轻人都知道3与1之比3就是无穷大的名言,应该说这种思想影响了当时很多人的科研方法。
彭先生擅长对复杂物理问题进行“粗估”,提出了很多粗估公式和方法,我们经常看到在他办公室里的一块大黑板上密密麻麻的写着粗估公式和计算结果。所谓“粗估”,就是根据所研究系统的物理特征和参数大小,包括近似求方程解的结果,估计出该系统各物理量的量级大小,以便较快抓住物理图象。这种方式,可以缩短研究周期,抓住物理本质,较快得出初步结论和建立初步物理模型,是十分重要的。我检验过彭先生的粗估,或者说保留主要项、舍弃次要项得出的微分方程近似解与精确解的差别有多大。结果表明,至少量级上是对的。当然,对于大科学的精确设计,最后还需要精确数值计算结果,以便给出精确的物理模型和设计参数。“粗估”的核心就是3与1之比3是无穷大的思想。它对于分析数值结果也是很有益的,可以帮助从大量的计算数据中分析得出物理结论。在彭先生和周光召、于敏等先生提倡和指导下,“粗估”成为当年理论部研究工作的重要手段之一,应该说它是我们理论部的一个传家宝。
保3舍1的处理问题方法,实质上就是分析复杂物理问题抓主要矛盾的方法。经常接触彭先生,他的这种分析和处理问题的思维和方式,对我有很大启发作用。我琢磨怎样用于我的研究实践,我可用一例子来比喻我的理解:比如你要研究一种动物,事先不知道它是什么,但如果你去掉很多因素后,计算出这种动物的鼻子很长,那只能是大象。这就抓住了最本质东西,你就可建立初步的物理模型。至于大象的鼻子正确长度多长、驱体多重等,那常常需进一步研究,包括数值计算。这件事看起来简单做起来不容易。你需要进行深入研究,很好了解物理背景和其中各个物理量的大小。对于一个复杂的物理系统,常常很多因素纠缠在一起,你需要分解各种因素,分别进行研究,抓住其中一个或几个关键因素的物理本质,然后研究它们之间的关联,最后进行集成。先从彭先生那里受到启发,后来又在周光召及于敏先生等领导下工作中受到启发,我自己不断琢磨这种思维方式。我深切感到向他们学习,不只是学他们求解物理问题的技巧,更重要的是学他们分析问题思维方法。我经常在讨论问题时听他们对问题的分析,经常反问我对这个问题是怎样分析的,我是怎样得出结论的,进行比较,从中悟出自己的不足,进行改进。书本知识是死的,你只要努力,容易学。但思维方法是活的,光学别人的招你不一定用得活,只有自己不断取人之长,不断体验,才能真正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思维方式。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会遇到一些同志,他们的思想很活跃,但缺乏正确的思维方式,自己抓不住要害,不能作出很好成绩来。可见正确思维方法的重要。
彭桓武先生十分重视数学基础,他说一个理论物理学家如果只有物理直观没有好的数学演算和解方程能力,不可能深入了解物理本质。他告诉我他在英国爱丁堡大学玻恩教授处做研究时,数学系教授Wittaker就是A course of modern analysis这本数学书的主要作者,另一位作者是Watson教授。彭先生说他读了此书和其中习题,收获很大,要我也学。所以我就在当年北京中国书店里买了一本影印的旧书回来,认认真真地学了不少内容,也做其中很多习题,我感到对我以后的研究工作帮助很大。此书我一直珍藏在书架内,有时还参考它。
2集体、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新、日日新
彭先生于1961年4月奉调到当时的二机部北京九所,顶替已撤走的苏联专家,负责核武器物理研究。他到所时正值原子弹设计的探索阶段。虽然原子弹这个名词大家都很熟悉,但由于美、苏等国高度保密,原子弹的详细物理过程我们需要自己摸索。当时唯一可供参考的内部资料是苏联总顾问向我国二机部部长介绍情况时的一份有关原子弹的极其简单的口授记录,因此,我国科学家只能自力更生、独立探索。彭先生的到来使这一探索工作如虎添翼。他把原子弹的爆炸过程分成了若干重要方面,进行物理分解研究,自己又计算又推导方程,然后给年轻人讲课,让更多人熟悉这些研究内容,进行研究。为了使学术讨论有共同用语,他把各种过程和物理特征的术语进行规范,诸如定容增殖、突变刹那等等。当时他主要集中在反应后高超临界条件下的物理过程的研究,包括裂变点火和能量释放估计。在研究与点火有关的冲击波聚焦出中子的物理问题时,他巧妙地把复杂的不定常流体简化为定常流处理,图像十分清楚,得出了很好的结论,至今仍给当时参加这一研究工作的同志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他物理概念十分清楚,物理直观强并对物理量量级大小有清楚的了解,这使他能快速抓住物理本质。他是位理论物理学家,擅长于解析处理,起初他不太相信计算机计算,但随着研究问题愈来愈复杂,计算机也愈来愈发展,他感到数值模拟的重要,于是积极支持数值模拟研究。
听老同志说,1961年至1962年年初原子弹设计曾一度陷入困境。理论计算得到的炸药爆炸后在内爆过程中产生的压力总是小于苏联专家曾给我方的数据,当时负责力学的专家担心计算结果有错,于是进行一次又一次的九次反复计算,但结果就是与苏方提供的数据不同。这就是著名的“九次计算”,原子弹设计一时陷入了困境。彭桓武先生为九次计算的讨论和改进提出过不少很好的主意。最后,周光召先生仔细检查了九次计算结果,认为数据没有问题,他用最大功原理证明苏联人的数据是错误的,从而结束了近一年左右的争论,使原子弹设计工作全面展开。彭先生十分高兴他从前的研究生处理问题的敏锐和智慧,后来曾几次提起此事。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是1964年10月16日爆炸的。两年零两个月后,1966年12月又成功地进行了氢弹原理试验,抢在了法国人的前面,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理论部投入全部力量进行氢弹探索,如果说突破原子弹早期,苏联专家曾给过我们一些简单的原子弹的信息,那么到了研制氢弹的时候,则没有任何可供参考的资料。我和几位同志当年曾在周光召先生领导下,调研了十几年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报纸和一些杂志,没有得到任何有意义的信息。突破氢弹完全是中国人自主创新的结果。
在研究原子弹期间,彭先生事实上已开始琢磨氢弹会是怎么样的?他把氢弹作用过程分成若干阶段的物理问题,供大家研究。1964年底起,在他指导下和邓稼先主任、周光召常务副主任、于敏副主任、黄祖洽副主任(1960年代初钱三强先生已安排黄祖洽和于敏领导一个组在原子能所探索氢弹原理,于敏带领一个组于1965年1月正式调入加盟九院理论部,黄祖洽已先于于敏调入理论部)等组织领导下全面开展了氢弹原理探索。整个理论部充分发扬学术民主,组织进行了各种学术讨论。无论刚出校门的年轻大学毕业生,还是著名的科学家,都投入到这种讨论,没有年龄与资历的界限,畅所欲言,共同探讨。晚上理论部大楼灯火辉煌,大家一直干到深夜还不肯回宿舍,党委书记不得不赶大家去睡觉。群策群力,献计献策,新的见解、相同的意见和不同的认识互相交流和争论,给我们留下了至今仍十分向往的珍贵回忆。彭先生当时是主管理论部的九院副院长,已过50岁的人了,与大家一起,发表他对氢弹原理的看法,与大家一起讨论,还经常给我们这些年轻人讲课。我记得一次在一个会议室里,彭先生在黑板上写他的计算结果和看法,讲完后,想退回到他原来座位上去,但意犹未尽,一边退一边面向黑板继续讲,结果原来的椅子已被专注听他讲的王淦昌先生不经意地动了一下,彭先生差一点坐了个空,可见当时讲的人和听的人都沉浸在专注思考的气氛中。在众多的集体讨论中,提出了不少有启发性的想法。彭先生集思广益、凝聚和综合出突破氢弹原理的几条可能的路。他的一贯的思维方法是每条路子都要探索到底,并且他认为“堵”住路子也是贡献,说明此路不通,可放心走另外路。他建议兵分三路,由周光召、于敏、黄祖洽各自负责一条路,分头进行探索。彭先生后来在一个场合上说过,他当时凝练了大家智慧,准备作三次战斗,事不过三,总可突破氢弹。
1965年下半年,于敏先生领导着一个小组去上海嘉定,通过对加强型原子弹的深入计算和系统分析,终于找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进一步对各个过程物理规律的研究和计算表明确实抓住了氢弹的牛鼻子。彭先生很高兴,他与理论部领导邓稼先等向上级报告,建议进行原理试验。上级批准后,经过几个组的日夜努力,设计出原理试验的氢弹装置,终于在1966年底通过热试验证实了原理。同时彭先生建议下一步进行全当量试验,建议当量为300万吨TNT左右。在他的建议下,1967年成功地进行了大威力氢弹试验。原子弹和氢弹试验成功,使彭先生深深体会到集体的智慧和力量是十分伟大的。他认为他顶替苏联专家的任务已完成,于1972年调回原子能研究所。
原子弹和氢弹研制需要研究解决大量物理、数学、力学等科学问题,也需要研究解决大量技术和工程问题。由于保密的原因,一些关键科学技术问题无法从文献、资料上获得,它的研制成功完全是中国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自主创新、探索、研究的结果。由于对突破原子弹与氢弹科学原理的贡献,1984年仍在九所工作的同事以彭桓武为首的十位科学家的名义申报并获得“原子弹、氢弹研究中的数学物理问题”自然科学一等奖。按国家规定奖状是每位得奖人一份,而奖章是由第一作者保存。当我们把奖章送去时,他坚决谢绝,并且再三强调这是集体的功劳,不应给个人。经过我们再三说明,他才留下奖章。然后他说:“奖章我收下了,这样奖章就是我的了,我把它送给九所。”随即找到一张纸,提笔在上面写了“集体、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新、日日新”,把奖章和题词都让来人带回了所里。我们所在有关核武器事业发展的几次内部展览会上都展出了彭先生的这一题字,参观的人在听了讲解后都十分感动,对这位德高望重的科学家深表敬佩。正如他这幅题词所表达的,每当有人与他谈起他在核武器研究中的功劳,或者媒体采访他时,他都会很严肃地说:都是大家干出来的。他的这种感情也充分表达在他于2001年发表的“彭桓武诗文集”中写的几首诗里。
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他十分激动,在罗布泊宴会上即兴写了一首感慨万分的七绝诗:“亭亭铁塔矗秋空,六亿人民愿望同。不是工农兵协力,焉得数理化成功。”1) 这首诗深情地歌颂了集体的力量,说明了没有大家的齐心协力,努力攻关,光靠我们搞理论研究设计是无法获得原子弹试验成功的。
1)这首及以下两首诗分别见:彭桓武,《物理天工总是鲜:彭桓武诗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3—4页接着在1965年5月4日五四青年节时,他以游香山为题作七律一首,歌颂集体的伟大作用:“半百芳华逝水流,几分暗淡几分稠。良辰最羡青年节,试步初登鬼见愁。盘路崎岖防失足,对山绿翠喜凝眸。雄心后进齐先进,钝骨频加激励油。”他在注释中说:第三、四句为在五四青年节时联想当时理论部以青年为大多数的集体首次试验原子弹成功,后四句联带描写当初探索氢弹时个人的心情。又一次强调了集体的作用。
突破氢弹17年后,他在1983年4月22日游西山时,从知春亭望西山有感作七律一首:“尘消气静远山明,地塑天雕骨肉盈。折皱峰峦掀广被,青葱树木筑长城。飞魂仿佛亲胸乳,望情依稀识颊睛,一经陡攀愁见鬼,似曾携侣御风行!”他在注释中说:望中西山如睡美人,隐喻祖国大地母亲。第五、六句描述她的爱子(隐指彭先生自己——笔者)的依恋之情。第七、八句联带描述集体胜利突破氢弹秘密之形象。再一次提到突破氢弹是集体之功。
他在总结突破原子弹、氢弹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搞大科学工程一定要依靠集体智慧的观点。例如,他十分关心热核聚变研究,热核研究已经历了50年,但目前仍未突破点火,而作为能源应用则估计要到21世纪中叶。为此他曾经向中国科学院领导建议我国的核聚变研究必须充分发挥集体的作用,希望组织专家像突破原子弹、氢弹那样发挥科学民主和依靠集体力量加快我国热核聚变研究进程。2004年10月初他生日那天,我和欧阳钟灿院士及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办公室主任赵世荣一起去看他时,他又提到组织集体攻关,依靠集体力量解决问题的重要性。
他自己从不居功,可对于别人作出过的贡献他从不忘记。彭先生得过几次大奖,特别是1995年的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获百万元奖金。他把这笔钱分成三万或几万不等的份额,寄往曾与他合作过的并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现在已过花甲之年的当年的年轻人,其中一些人后来已离开所,分布在全国各地,已较长时期没有联系,他千方百计设法搞到地址,把钱寄给他们作为纪念。
3虚怀若谷 厚待他人
彭先生是一位大科学家,可他从没有一点大科学家的架子。你去请教和讨论问题,总是平等待人,表面上丝毫看不出是位知识渊博、成就卓著的人。我年轻时去找他,起初不免有点拘束,感到他是父辈的人,又是大科学家。但一接触后这种顾虑立刻消失,感到他很慈祥,鼓励你提问题,并把问题解讲得很清楚,经常在他办公室内的一块大黑板上详细推导给你看。他经常给我们作报告,讲他的研究结果,你可以打断他的报告,随时提问。我有过多次体会,不管我有时提的问题有多可笑,或者甚至不同意他的看法,他从不盛气凌人,总是与你讨论、讲解,获得共识。有时他认为你的意见是对的时候,就会很快放弃他的看法。他多次说过科学认识常常需要从争论中获得。在突破氢弹前夕的一次讨论中,我印象十分深。彭先生正在讲他的新想法,有一位刚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认为彭先生讲的跟他的想法一样,就冒失地冲着彭先生嚷:“彭公呀!你的思想已包含在我的思想里了”。我们当时以为彭先生会不高兴,然而彭先生虚怀若谷并没有表示出丝毫不快之意。另外一个例子是在1969年第一次地下核试验现场。当时正在讨论一个坑道自封的力学问题,彭先生在讲他的计算,专家们都在听他讲。这时于敏先生感到计算有问题,便很谦虚地跟彭先生说:“我给您作些补充”。彭先生听完他的“补充”后,立刻意识到自己的计算有问题,便在大家面前毫不犹豫地说:“老于说得对,就按老于的方法办。”2),一点也没有感到架子放不下来的尴尬样子。我们现在谈起30多年前彭先生这种虚怀若谷、服从真理的态度,仍然被此事深深感动。一个人无论你水平怎么高,总会有所疏忽和失误,兼听则明,才会使自己更加提高和使周围人更加受益。
彭先生也常与我们谈起,一位受人尊重的人不要以自己的意见压人;另一方面,他说别人也不能太相信权威,这对研究工作十分不利。他在1993年《现代物理知识》上发表的一篇文章3)谈到:德布罗意提出波粒二象性得了诺贝尔奖后,他的意见几乎左右了当时法国物理学的发展,使得一段时间内法国理论物理变得落后。这段历史教训的总结使彭先生自己十分谨慎,不要因自己的意见而对国家和集体造成影响。他还告诫我们对科研工作不能人云亦云,在继承人家结论时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他仍举例德国的海森堡在研究反应堆时的工作,海森堡研究结果认为铀、石墨均匀混合不行,作了此路不通的结论。美国科学家费米研究后认为:铀、石墨作成棒后非均匀分布就行了,从而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反应堆。所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很重要。彭先生认为海森堡的这种错误可能也是当年希特勒没造出原子弹的原因。
2)理论部有一个很好的传统,都以老邓、老周、老于……称主任和副主任,年青人与科学家、下级与上级关系十分融洽。
3)见彭桓武,《物理天工总是鲜:彭桓武诗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64页人们十分尊重彭先生的学识和为人,他在原子能所时人们尊称他为彭公,1961年到我们所后不少同志仍称他彭公。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有人贴了彭先生一张大字报,意思是彭公是四旧,应批判。彭先生从来不写什么大字报,这时却写了一份恐怕是空前绝后的大字报,以“粪土当年万户侯”为题,表明“公侯伯子男是封建四旧应去掉,大家都以同志相称就可以了”。他平时与大家相处非常随和,没有任何架子,不喜欢突出自己。
彭先生尊重科学,坚持真理,不被政治批判所屈服。1969年8、9月份,彭先生与王淦昌先生一起去第一次地下核试验现场指导工作。我国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是在平洞(从山脚沿水平线挖成洞)中进行,核装置就放在洞中坑道终端鱼钩型爆室内。试前工作人员要进入洞内在爆室周围放置很多测试仪器。有一次王淦昌先生与一位负责安装核装置的工人师傅进洞作业,那位师傅身上带有剂量笔,一进入洞内便听到计数器不断地响,知道有放射性气体。经检测后,发现洞内氡气浓度远远高于标准。洞内不仅有我们的作业人员而且还有基地的解放军战士,这么高浓度的氡气对人体是很有害的。出于科学家的良知和责任性,王淦昌先生联合彭先生向当时核试验基地的白司令员建议,加强洞内通风降低氡气浓度。然而出乎意外,白司令拒绝了这一建议,说有点气体有什么了不起,扰乱了军心,要批判“活命哲学”。这位司令为了表示自己不怕死,还亲自进洞内与战士一起吃午饭。当时文化大革命正酣,这给王、彭两位先生造成了压力,但他们仍然坚持真理,认为要尊重科学,要珍惜工作人员的健康。因为这件事,结合批判学术权威,我们所的政委(当时我们是军管单位,所长、政委、室的领导都是军人)在一次大会上半点名地批判说“什么‘公’,什么‘老师’(当时大家尊称王淦昌为‘王老师’),摇着鹅毛扇,踏着八字步……”,暗示王、彭两人出坏主意,蛊惑人心。王、彭二位先生从来光明磊落,没想到会受此污蔑。他们当然不会在这种压力下低头、认错。
彭先生有很多鲜为人知的关怀和关心他人的故事,当年在他领导下的不少同志都亲身感受过他的关怀。我印象很深的一次是彭先生和我们一起在青海我们九院的总部出差,我高原(海拔3000米)反应很大,睡不好也吃不好,感觉上非常不好受。在向院领导汇报我们组有关第一次地下核试验的工作时,感到要呕吐,我自己强忍着想继续作完报告,彭先生注意到我的脸色不好和难受劲,就说:“贺贤土看样子身体不好,不要再报告下去,快去休息”。我当时心里很感动,想不到平时话语不多、一心扑在科学上的彭先生如此细心和关怀人。
另外一件事给我的印象也十分深。在一次学术报告会上,报告人提出了状态方程的一个问题,认为需要认真研究。不等他讲完,旁边一位年轻的同志就冲着报告人说:“这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意思是没有必要研究。彭先生当时在场,认为这位同志这样发表意见不妥,批评那位同志说话要谦虚一些,不要轻率下结论,要等人把话讲完,才有利于深入讨论问题。彭先生的批评使会场的气氛一下子凝结起来,那位年轻人也感到很不自在。后来领导也找了他谈话,年轻人感到有压力。几天以后的星期天,彭先生刚好在颐和园遇到他,主动过去和他交谈并一起游览。交谈中先对他说自己在会场上话可能说重了,对不起。然后平和地开导:作为一位科学工作者,要充分了解人家的意见,在尊重人家基础上谦虚地提出问题,轻率地下结论很可能会把一个重要问题给漏掉了。彭先生的諄諄开导,使当年的那位年轻人,现在谈起这件事还深深感到彭先生对他的关心与帮助。
彭先生生活十分俭朴,对自己生活要求很低。他的衣著十分随便,一套衣服穿了又穿,十分旧了仍然舍不得丢掉。但看到别人生活有困难,他就会毫不犹豫地伸出友谊之手,不少人都接受过他经济上的帮助。特别是他熟悉的老同事和老同事的子女,他经常问他们有没有困难,进行接济。这里有一个故事:1969年我们所一位同志调往东北老家工作,托运东西需一笔钱,向彭先生借30元钱(我们当时的月工资为56元)。彭先生虽对他不太熟,但慨然应允,这笔钱后来彭先生也没要他还。
彭先生从不居功自傲,向组织索求些什么,他也极不愿意麻烦别人。前些年他经常去游香山。80多岁老人自己挤公共汽车,我多次劝他千万不要一个人去,如要去,理论物理所和我们所都可派车送,我说你为我国核武器事业作出那么多贡献,派车是应该的,可他总是摇摇头。他说坐公共汽车时还可锻炼身体,手拉着车上防摔的圆环可以锻炼胳膊。他向我摇晃一下自己的手臂,说:你看我的胳膊多结实,说着他自己也乐了。20世纪80年代末,他已是72岁的人了,计划去云南看望当年与他一起创建云南大学物理系的一位故人,同时去扫他的姐姐的墓。一个偶然机会,此事被我所一位老家在云南的同志知道了。他感到彭先生是著名的科学家,已经72岁了,又只身前往,应该请云南有关部门接待一下。于是在彭先生不知情的情况下,报告了云南省科技厅,云南省作了热情接待。事后云南接待的同志很感慨地说:彭先生没有一点大科学家的架子,平易近人,很怕麻烦我们,问他安排上有什么要求,他什么也不提,真是一位朴实谦逊的大科学家。
有人曾这样描述彭先生:“他虚怀若谷,心地光明,无求于人,无欲于世,一副安然自得的悠然模样,仿佛泰山崩于前也面不改色心不跳。他把全部精力献给了自然科学。”。可是一旦国家需要他从事核武器研究,他会毫不犹豫地说出“国家需要,我去!” “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旦旦信誓,这就是彭桓武。”4)。从我与彭先生的多年接触中,我深深感受到这些话非常确切地评价了彭先生其人。
我于1962年11月底进入北京九所(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身)从事核武器物理研究。1963年初,进所后不久的一天,组长通知我们去听彭桓武先生给我们上的第一堂课。在大学学习时,老师就谈到彭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受人尊敬的理论物理学家,能听他讲课,感到十分荣幸。听课的人除了我们几位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和组内几位老同志外,还有我当时不认识的一位年长学者也来了。眼前的彭先生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个子不高、讲课声音较低、很随和、穿着朴素的一位“平凡”的科学家。彭先生讲课内容是关于随时间变化的γ射线点源在空气中的深穿透问题,需要研究多次散射、大能量慢化等过程,计算比较复杂。他的讲课不同于在学校时教师授课的方式,他一边讲γ射点穿透的难点,详细推导公式和具体计算,一边总是启发我们提问。由于我们在学校时习惯于听老师讲,比较胆怯,不敢提问题,但那位年长的学者(后来才知道是程开甲先生)则不断地向彭先生提问题和进行讨论,两人有时甚至争论得很剧烈。我感到这样讲课十分新奇,听讲时理解不深或似懂非懂的一些问题,经他们一讨论,感到明白了不少。我很感兴趣这样的讲课和听课方式。受了彭先生第一次讲课及后来几次讲课的启发,慢慢地我也学会在别人讲课和作报告时积极思考问题,大胆提问和发表自己意见,从中收益匪浅。
我与彭先生进一步接触是在1963年下半年,当时我从事了一项新的工作,研究由于外界突发因素的影响,在高超临界下系统还没达到设定的点火时刻以前,发生过早点火的概率,也就是研究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1964年上半年我们搬到新落成的14号楼办公,刚好与彭先生的办公室在同一层楼。由于我对彭先生讲课时的随和态度和讨论问题解答问题的作风印象很深,感到他没有大科学家架子,所以经常找他请教研究中遇到的问题。我所研究的方程是一个非线性积分微分方程,性质比较特殊,不同于一般的偏微分方程,自然无法求得精确解析解,需要作不同近似下的解。我对近似解是否可靠心里没底,常常找他讨论。他对这类特殊方程也很感兴趣,加上第一颗原子弹计划下半年试验,计算过早点火概率大小是一个重要问题,所以他对过早点火研究很关心。为了深入了解这个方程的基本性质,在他指点下,我从生成函数出发,仔细推导得到了有关中子与原子核各种相互作用的生成函数的方程,并在特定近似下获得了现在所用方程,写成了详细论文给他看。他看了很高兴,并指出了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我心里十分庆幸,参加工作后不久,就得到名师的指点。这个工作不到一年时间就完成了任务,并提供了物理模型由数学组的同志编成程序进行精确数值计算,为核试验提供了数据。他对这一工作一直很关心, 1970年代末他离开我们所时,还把他以前研究有关点火的稿子留下给我。
随着跟他接触增多,我发现彭先生有一个很大的本领,一个复杂的微分方程到他手里,他能很快估计出方程各项的相对大小,然后把小数的项去掉,保留大数项。在保留或舍弃一些项时,他形象地比喻为3与1之比,3就是无穷大,意思是1完全可忽略。经他这么一处理,一个复杂的微分方程就常常容易得到近似解,甚至变成一个特殊函数方程,解自然就出来了。当年的很多年轻人都知道3与1之比3就是无穷大的名言,应该说这种思想影响了当时很多人的科研方法。
彭先生擅长对复杂物理问题进行“粗估”,提出了很多粗估公式和方法,我们经常看到在他办公室里的一块大黑板上密密麻麻的写着粗估公式和计算结果。所谓“粗估”,就是根据所研究系统的物理特征和参数大小,包括近似求方程解的结果,估计出该系统各物理量的量级大小,以便较快抓住物理图象。这种方式,可以缩短研究周期,抓住物理本质,较快得出初步结论和建立初步物理模型,是十分重要的。我检验过彭先生的粗估,或者说保留主要项、舍弃次要项得出的微分方程近似解与精确解的差别有多大。结果表明,至少量级上是对的。当然,对于大科学的精确设计,最后还需要精确数值计算结果,以便给出精确的物理模型和设计参数。“粗估”的核心就是3与1之比3是无穷大的思想。它对于分析数值结果也是很有益的,可以帮助从大量的计算数据中分析得出物理结论。在彭先生和周光召、于敏等先生提倡和指导下,“粗估”成为当年理论部研究工作的重要手段之一,应该说它是我们理论部的一个传家宝。
保3舍1的处理问题方法,实质上就是分析复杂物理问题抓主要矛盾的方法。经常接触彭先生,他的这种分析和处理问题的思维和方式,对我有很大启发作用。我琢磨怎样用于我的研究实践,我可用一例子来比喻我的理解:比如你要研究一种动物,事先不知道它是什么,但如果你去掉很多因素后,计算出这种动物的鼻子很长,那只能是大象。这就抓住了最本质东西,你就可建立初步的物理模型。至于大象的鼻子正确长度多长、驱体多重等,那常常需进一步研究,包括数值计算。这件事看起来简单做起来不容易。你需要进行深入研究,很好了解物理背景和其中各个物理量的大小。对于一个复杂的物理系统,常常很多因素纠缠在一起,你需要分解各种因素,分别进行研究,抓住其中一个或几个关键因素的物理本质,然后研究它们之间的关联,最后进行集成。先从彭先生那里受到启发,后来又在周光召及于敏先生等领导下工作中受到启发,我自己不断琢磨这种思维方式。我深切感到向他们学习,不只是学他们求解物理问题的技巧,更重要的是学他们分析问题思维方法。我经常在讨论问题时听他们对问题的分析,经常反问我对这个问题是怎样分析的,我是怎样得出结论的,进行比较,从中悟出自己的不足,进行改进。书本知识是死的,你只要努力,容易学。但思维方法是活的,光学别人的招你不一定用得活,只有自己不断取人之长,不断体验,才能真正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思维方式。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会遇到一些同志,他们的思想很活跃,但缺乏正确的思维方式,自己抓不住要害,不能作出很好成绩来。可见正确思维方法的重要。
彭桓武先生十分重视数学基础,他说一个理论物理学家如果只有物理直观没有好的数学演算和解方程能力,不可能深入了解物理本质。他告诉我他在英国爱丁堡大学玻恩教授处做研究时,数学系教授Wittaker就是A course of modern analysis这本数学书的主要作者,另一位作者是Watson教授。彭先生说他读了此书和其中习题,收获很大,要我也学。所以我就在当年北京中国书店里买了一本影印的旧书回来,认认真真地学了不少内容,也做其中很多习题,我感到对我以后的研究工作帮助很大。此书我一直珍藏在书架内,有时还参考它。
2集体、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新、日日新
彭先生于1961年4月奉调到当时的二机部北京九所,顶替已撤走的苏联专家,负责核武器物理研究。他到所时正值原子弹设计的探索阶段。虽然原子弹这个名词大家都很熟悉,但由于美、苏等国高度保密,原子弹的详细物理过程我们需要自己摸索。当时唯一可供参考的内部资料是苏联总顾问向我国二机部部长介绍情况时的一份有关原子弹的极其简单的口授记录,因此,我国科学家只能自力更生、独立探索。彭先生的到来使这一探索工作如虎添翼。他把原子弹的爆炸过程分成了若干重要方面,进行物理分解研究,自己又计算又推导方程,然后给年轻人讲课,让更多人熟悉这些研究内容,进行研究。为了使学术讨论有共同用语,他把各种过程和物理特征的术语进行规范,诸如定容增殖、突变刹那等等。当时他主要集中在反应后高超临界条件下的物理过程的研究,包括裂变点火和能量释放估计。在研究与点火有关的冲击波聚焦出中子的物理问题时,他巧妙地把复杂的不定常流体简化为定常流处理,图像十分清楚,得出了很好的结论,至今仍给当时参加这一研究工作的同志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他物理概念十分清楚,物理直观强并对物理量量级大小有清楚的了解,这使他能快速抓住物理本质。他是位理论物理学家,擅长于解析处理,起初他不太相信计算机计算,但随着研究问题愈来愈复杂,计算机也愈来愈发展,他感到数值模拟的重要,于是积极支持数值模拟研究。
听老同志说,1961年至1962年年初原子弹设计曾一度陷入困境。理论计算得到的炸药爆炸后在内爆过程中产生的压力总是小于苏联专家曾给我方的数据,当时负责力学的专家担心计算结果有错,于是进行一次又一次的九次反复计算,但结果就是与苏方提供的数据不同。这就是著名的“九次计算”,原子弹设计一时陷入了困境。彭桓武先生为九次计算的讨论和改进提出过不少很好的主意。最后,周光召先生仔细检查了九次计算结果,认为数据没有问题,他用最大功原理证明苏联人的数据是错误的,从而结束了近一年左右的争论,使原子弹设计工作全面展开。彭先生十分高兴他从前的研究生处理问题的敏锐和智慧,后来曾几次提起此事。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是1964年10月16日爆炸的。两年零两个月后,1966年12月又成功地进行了氢弹原理试验,抢在了法国人的前面,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理论部投入全部力量进行氢弹探索,如果说突破原子弹早期,苏联专家曾给过我们一些简单的原子弹的信息,那么到了研制氢弹的时候,则没有任何可供参考的资料。我和几位同志当年曾在周光召先生领导下,调研了十几年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报纸和一些杂志,没有得到任何有意义的信息。突破氢弹完全是中国人自主创新的结果。
在研究原子弹期间,彭先生事实上已开始琢磨氢弹会是怎么样的?他把氢弹作用过程分成若干阶段的物理问题,供大家研究。1964年底起,在他指导下和邓稼先主任、周光召常务副主任、于敏副主任、黄祖洽副主任(1960年代初钱三强先生已安排黄祖洽和于敏领导一个组在原子能所探索氢弹原理,于敏带领一个组于1965年1月正式调入加盟九院理论部,黄祖洽已先于于敏调入理论部)等组织领导下全面开展了氢弹原理探索。整个理论部充分发扬学术民主,组织进行了各种学术讨论。无论刚出校门的年轻大学毕业生,还是著名的科学家,都投入到这种讨论,没有年龄与资历的界限,畅所欲言,共同探讨。晚上理论部大楼灯火辉煌,大家一直干到深夜还不肯回宿舍,党委书记不得不赶大家去睡觉。群策群力,献计献策,新的见解、相同的意见和不同的认识互相交流和争论,给我们留下了至今仍十分向往的珍贵回忆。彭先生当时是主管理论部的九院副院长,已过50岁的人了,与大家一起,发表他对氢弹原理的看法,与大家一起讨论,还经常给我们这些年轻人讲课。我记得一次在一个会议室里,彭先生在黑板上写他的计算结果和看法,讲完后,想退回到他原来座位上去,但意犹未尽,一边退一边面向黑板继续讲,结果原来的椅子已被专注听他讲的王淦昌先生不经意地动了一下,彭先生差一点坐了个空,可见当时讲的人和听的人都沉浸在专注思考的气氛中。在众多的集体讨论中,提出了不少有启发性的想法。彭先生集思广益、凝聚和综合出突破氢弹原理的几条可能的路。他的一贯的思维方法是每条路子都要探索到底,并且他认为“堵”住路子也是贡献,说明此路不通,可放心走另外路。他建议兵分三路,由周光召、于敏、黄祖洽各自负责一条路,分头进行探索。彭先生后来在一个场合上说过,他当时凝练了大家智慧,准备作三次战斗,事不过三,总可突破氢弹。
1965年下半年,于敏先生领导着一个小组去上海嘉定,通过对加强型原子弹的深入计算和系统分析,终于找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进一步对各个过程物理规律的研究和计算表明确实抓住了氢弹的牛鼻子。彭先生很高兴,他与理论部领导邓稼先等向上级报告,建议进行原理试验。上级批准后,经过几个组的日夜努力,设计出原理试验的氢弹装置,终于在1966年底通过热试验证实了原理。同时彭先生建议下一步进行全当量试验,建议当量为300万吨TNT左右。在他的建议下,1967年成功地进行了大威力氢弹试验。原子弹和氢弹试验成功,使彭先生深深体会到集体的智慧和力量是十分伟大的。他认为他顶替苏联专家的任务已完成,于1972年调回原子能研究所。
原子弹和氢弹研制需要研究解决大量物理、数学、力学等科学问题,也需要研究解决大量技术和工程问题。由于保密的原因,一些关键科学技术问题无法从文献、资料上获得,它的研制成功完全是中国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自主创新、探索、研究的结果。由于对突破原子弹与氢弹科学原理的贡献,1984年仍在九所工作的同事以彭桓武为首的十位科学家的名义申报并获得“原子弹、氢弹研究中的数学物理问题”自然科学一等奖。按国家规定奖状是每位得奖人一份,而奖章是由第一作者保存。当我们把奖章送去时,他坚决谢绝,并且再三强调这是集体的功劳,不应给个人。经过我们再三说明,他才留下奖章。然后他说:“奖章我收下了,这样奖章就是我的了,我把它送给九所。”随即找到一张纸,提笔在上面写了“集体、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新、日日新”,把奖章和题词都让来人带回了所里。我们所在有关核武器事业发展的几次内部展览会上都展出了彭先生的这一题字,参观的人在听了讲解后都十分感动,对这位德高望重的科学家深表敬佩。正如他这幅题词所表达的,每当有人与他谈起他在核武器研究中的功劳,或者媒体采访他时,他都会很严肃地说:都是大家干出来的。他的这种感情也充分表达在他于2001年发表的“彭桓武诗文集”中写的几首诗里。
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他十分激动,在罗布泊宴会上即兴写了一首感慨万分的七绝诗:“亭亭铁塔矗秋空,六亿人民愿望同。不是工农兵协力,焉得数理化成功。”1) 这首诗深情地歌颂了集体的力量,说明了没有大家的齐心协力,努力攻关,光靠我们搞理论研究设计是无法获得原子弹试验成功的。
1)这首及以下两首诗分别见:彭桓武,《物理天工总是鲜:彭桓武诗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3—4页接着在1965年5月4日五四青年节时,他以游香山为题作七律一首,歌颂集体的伟大作用:“半百芳华逝水流,几分暗淡几分稠。良辰最羡青年节,试步初登鬼见愁。盘路崎岖防失足,对山绿翠喜凝眸。雄心后进齐先进,钝骨频加激励油。”他在注释中说:第三、四句为在五四青年节时联想当时理论部以青年为大多数的集体首次试验原子弹成功,后四句联带描写当初探索氢弹时个人的心情。又一次强调了集体的作用。
突破氢弹17年后,他在1983年4月22日游西山时,从知春亭望西山有感作七律一首:“尘消气静远山明,地塑天雕骨肉盈。折皱峰峦掀广被,青葱树木筑长城。飞魂仿佛亲胸乳,望情依稀识颊睛,一经陡攀愁见鬼,似曾携侣御风行!”他在注释中说:望中西山如睡美人,隐喻祖国大地母亲。第五、六句描述她的爱子(隐指彭先生自己——笔者)的依恋之情。第七、八句联带描述集体胜利突破氢弹秘密之形象。再一次提到突破氢弹是集体之功。
他在总结突破原子弹、氢弹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搞大科学工程一定要依靠集体智慧的观点。例如,他十分关心热核聚变研究,热核研究已经历了50年,但目前仍未突破点火,而作为能源应用则估计要到21世纪中叶。为此他曾经向中国科学院领导建议我国的核聚变研究必须充分发挥集体的作用,希望组织专家像突破原子弹、氢弹那样发挥科学民主和依靠集体力量加快我国热核聚变研究进程。2004年10月初他生日那天,我和欧阳钟灿院士及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办公室主任赵世荣一起去看他时,他又提到组织集体攻关,依靠集体力量解决问题的重要性。
他自己从不居功,可对于别人作出过的贡献他从不忘记。彭先生得过几次大奖,特别是1995年的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获百万元奖金。他把这笔钱分成三万或几万不等的份额,寄往曾与他合作过的并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现在已过花甲之年的当年的年轻人,其中一些人后来已离开所,分布在全国各地,已较长时期没有联系,他千方百计设法搞到地址,把钱寄给他们作为纪念。
3虚怀若谷 厚待他人
彭先生是一位大科学家,可他从没有一点大科学家的架子。你去请教和讨论问题,总是平等待人,表面上丝毫看不出是位知识渊博、成就卓著的人。我年轻时去找他,起初不免有点拘束,感到他是父辈的人,又是大科学家。但一接触后这种顾虑立刻消失,感到他很慈祥,鼓励你提问题,并把问题解讲得很清楚,经常在他办公室内的一块大黑板上详细推导给你看。他经常给我们作报告,讲他的研究结果,你可以打断他的报告,随时提问。我有过多次体会,不管我有时提的问题有多可笑,或者甚至不同意他的看法,他从不盛气凌人,总是与你讨论、讲解,获得共识。有时他认为你的意见是对的时候,就会很快放弃他的看法。他多次说过科学认识常常需要从争论中获得。在突破氢弹前夕的一次讨论中,我印象十分深。彭先生正在讲他的新想法,有一位刚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认为彭先生讲的跟他的想法一样,就冒失地冲着彭先生嚷:“彭公呀!你的思想已包含在我的思想里了”。我们当时以为彭先生会不高兴,然而彭先生虚怀若谷并没有表示出丝毫不快之意。另外一个例子是在1969年第一次地下核试验现场。当时正在讨论一个坑道自封的力学问题,彭先生在讲他的计算,专家们都在听他讲。这时于敏先生感到计算有问题,便很谦虚地跟彭先生说:“我给您作些补充”。彭先生听完他的“补充”后,立刻意识到自己的计算有问题,便在大家面前毫不犹豫地说:“老于说得对,就按老于的方法办。”2),一点也没有感到架子放不下来的尴尬样子。我们现在谈起30多年前彭先生这种虚怀若谷、服从真理的态度,仍然被此事深深感动。一个人无论你水平怎么高,总会有所疏忽和失误,兼听则明,才会使自己更加提高和使周围人更加受益。
彭先生也常与我们谈起,一位受人尊重的人不要以自己的意见压人;另一方面,他说别人也不能太相信权威,这对研究工作十分不利。他在1993年《现代物理知识》上发表的一篇文章3)谈到:德布罗意提出波粒二象性得了诺贝尔奖后,他的意见几乎左右了当时法国物理学的发展,使得一段时间内法国理论物理变得落后。这段历史教训的总结使彭先生自己十分谨慎,不要因自己的意见而对国家和集体造成影响。他还告诫我们对科研工作不能人云亦云,在继承人家结论时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他仍举例德国的海森堡在研究反应堆时的工作,海森堡研究结果认为铀、石墨均匀混合不行,作了此路不通的结论。美国科学家费米研究后认为:铀、石墨作成棒后非均匀分布就行了,从而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反应堆。所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很重要。彭先生认为海森堡的这种错误可能也是当年希特勒没造出原子弹的原因。
2)理论部有一个很好的传统,都以老邓、老周、老于……称主任和副主任,年青人与科学家、下级与上级关系十分融洽。
3)见彭桓武,《物理天工总是鲜:彭桓武诗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64页人们十分尊重彭先生的学识和为人,他在原子能所时人们尊称他为彭公,1961年到我们所后不少同志仍称他彭公。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有人贴了彭先生一张大字报,意思是彭公是四旧,应批判。彭先生从来不写什么大字报,这时却写了一份恐怕是空前绝后的大字报,以“粪土当年万户侯”为题,表明“公侯伯子男是封建四旧应去掉,大家都以同志相称就可以了”。他平时与大家相处非常随和,没有任何架子,不喜欢突出自己。
彭先生尊重科学,坚持真理,不被政治批判所屈服。1969年8、9月份,彭先生与王淦昌先生一起去第一次地下核试验现场指导工作。我国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是在平洞(从山脚沿水平线挖成洞)中进行,核装置就放在洞中坑道终端鱼钩型爆室内。试前工作人员要进入洞内在爆室周围放置很多测试仪器。有一次王淦昌先生与一位负责安装核装置的工人师傅进洞作业,那位师傅身上带有剂量笔,一进入洞内便听到计数器不断地响,知道有放射性气体。经检测后,发现洞内氡气浓度远远高于标准。洞内不仅有我们的作业人员而且还有基地的解放军战士,这么高浓度的氡气对人体是很有害的。出于科学家的良知和责任性,王淦昌先生联合彭先生向当时核试验基地的白司令员建议,加强洞内通风降低氡气浓度。然而出乎意外,白司令拒绝了这一建议,说有点气体有什么了不起,扰乱了军心,要批判“活命哲学”。这位司令为了表示自己不怕死,还亲自进洞内与战士一起吃午饭。当时文化大革命正酣,这给王、彭两位先生造成了压力,但他们仍然坚持真理,认为要尊重科学,要珍惜工作人员的健康。因为这件事,结合批判学术权威,我们所的政委(当时我们是军管单位,所长、政委、室的领导都是军人)在一次大会上半点名地批判说“什么‘公’,什么‘老师’(当时大家尊称王淦昌为‘王老师’),摇着鹅毛扇,踏着八字步……”,暗示王、彭两人出坏主意,蛊惑人心。王、彭二位先生从来光明磊落,没想到会受此污蔑。他们当然不会在这种压力下低头、认错。
彭先生有很多鲜为人知的关怀和关心他人的故事,当年在他领导下的不少同志都亲身感受过他的关怀。我印象很深的一次是彭先生和我们一起在青海我们九院的总部出差,我高原(海拔3000米)反应很大,睡不好也吃不好,感觉上非常不好受。在向院领导汇报我们组有关第一次地下核试验的工作时,感到要呕吐,我自己强忍着想继续作完报告,彭先生注意到我的脸色不好和难受劲,就说:“贺贤土看样子身体不好,不要再报告下去,快去休息”。我当时心里很感动,想不到平时话语不多、一心扑在科学上的彭先生如此细心和关怀人。
另外一件事给我的印象也十分深。在一次学术报告会上,报告人提出了状态方程的一个问题,认为需要认真研究。不等他讲完,旁边一位年轻的同志就冲着报告人说:“这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意思是没有必要研究。彭先生当时在场,认为这位同志这样发表意见不妥,批评那位同志说话要谦虚一些,不要轻率下结论,要等人把话讲完,才有利于深入讨论问题。彭先生的批评使会场的气氛一下子凝结起来,那位年轻人也感到很不自在。后来领导也找了他谈话,年轻人感到有压力。几天以后的星期天,彭先生刚好在颐和园遇到他,主动过去和他交谈并一起游览。交谈中先对他说自己在会场上话可能说重了,对不起。然后平和地开导:作为一位科学工作者,要充分了解人家的意见,在尊重人家基础上谦虚地提出问题,轻率地下结论很可能会把一个重要问题给漏掉了。彭先生的諄諄开导,使当年的那位年轻人,现在谈起这件事还深深感到彭先生对他的关心与帮助。
彭先生生活十分俭朴,对自己生活要求很低。他的衣著十分随便,一套衣服穿了又穿,十分旧了仍然舍不得丢掉。但看到别人生活有困难,他就会毫不犹豫地伸出友谊之手,不少人都接受过他经济上的帮助。特别是他熟悉的老同事和老同事的子女,他经常问他们有没有困难,进行接济。这里有一个故事:1969年我们所一位同志调往东北老家工作,托运东西需一笔钱,向彭先生借30元钱(我们当时的月工资为56元)。彭先生虽对他不太熟,但慨然应允,这笔钱后来彭先生也没要他还。
彭先生从不居功自傲,向组织索求些什么,他也极不愿意麻烦别人。前些年他经常去游香山。80多岁老人自己挤公共汽车,我多次劝他千万不要一个人去,如要去,理论物理所和我们所都可派车送,我说你为我国核武器事业作出那么多贡献,派车是应该的,可他总是摇摇头。他说坐公共汽车时还可锻炼身体,手拉着车上防摔的圆环可以锻炼胳膊。他向我摇晃一下自己的手臂,说:你看我的胳膊多结实,说着他自己也乐了。20世纪80年代末,他已是72岁的人了,计划去云南看望当年与他一起创建云南大学物理系的一位故人,同时去扫他的姐姐的墓。一个偶然机会,此事被我所一位老家在云南的同志知道了。他感到彭先生是著名的科学家,已经72岁了,又只身前往,应该请云南有关部门接待一下。于是在彭先生不知情的情况下,报告了云南省科技厅,云南省作了热情接待。事后云南接待的同志很感慨地说:彭先生没有一点大科学家的架子,平易近人,很怕麻烦我们,问他安排上有什么要求,他什么也不提,真是一位朴实谦逊的大科学家。
有人曾这样描述彭先生:“他虚怀若谷,心地光明,无求于人,无欲于世,一副安然自得的悠然模样,仿佛泰山崩于前也面不改色心不跳。他把全部精力献给了自然科学。”。可是一旦国家需要他从事核武器研究,他会毫不犹豫地说出“国家需要,我去!” “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旦旦信誓,这就是彭桓武。”4)。从我与彭先生的多年接触中,我深深感受到这些话非常确切地评价了彭先生其人。
附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