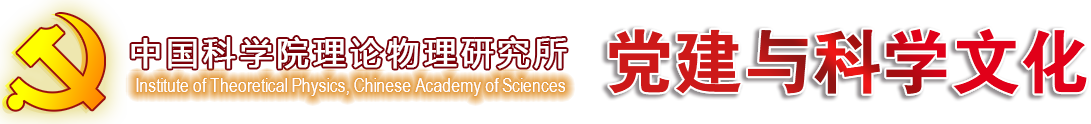大家风范
陈能宽:四十年情缘 弹指一挥间
来源:科学时报
时间:2007-03-06
| 2006年4月,陈能宽不幸摔伤了腿,股骨脱臼,一年多来很少走动。3月2日下午,当他在北京出席一个很重要的会议时,噩耗传来:彭公走了!那位与他共度“两弹一星”日夜的忘年交、那位朴实的长者、那位曾与他有10年诗词缘的彭公永远地离开了,他再也不能听到彭公亲切地喊他“老陈”了。 噩耗来得那么突然。 “如果彭公身体还可以,他一定也会出席这个会。”陈能宽一听说记者要采访关于彭桓武的事,立刻答应。开完4个小时的会后,他匆忙吃了晚饭就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彭公比我大近十岁。我上世纪60年代从美国回国进当时的二机部第九研究所时,彭公是副所长。他是长者,也是我的领导。我把他当老师,而他可不把自己当老师,他叫我‘老陈’,我称他‘彭公’。他非常随和,别人都这么叫他。”陈能宽脸上泛起了亲切的笑容。 陈能宽和彭桓武一样都是“两弹一星”元勋。当时,他们一个搞试验,一个搞理论。一样的科学理想、一样的科学目标让他们走到了一起,他们的友谊也从此开始。 陈能宽说,彭桓武虽然是搞理论的,但对试验也很关心,他们经常在一起交流科学问题。 “很多人都以为我们在一起只会谈科学谈研究,其实我们的话题很多,即使是在做‘两弹一星’研究的时候。我们在一起从来不会冷场,都是抢着说话,从科学问题到诗词,甚至到天文地理、宗教。偶尔也会拉家常,他给我讲他的父亲、爱人、儿子……” 陈能宽说,其中,有一个问题是他们每次闲谈或谈话必不可少的,就是关于年轻人的培养。“彭桓武常说,摸爬滚打应该是在年轻的时候,年纪大了,心有余而力不足。年纪大的人就做两件事:一是把握方向,让年轻人少走弯路;其次是培养年轻人,不光是技术方面,也要在道德品质、修养方面进行培养。” 彭桓武和陈能宽都有一个爱好就是喜好格律诗词,谈诗赋对是两位老人一生的乐趣。1996年,陈能宽写了一幅对联,上联是:“回顾三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他对自己的下联不满意,就把上联寄给了彭桓武,彭桓武回应:“俯瞻洞庭湖内外,乾坤日夜浮:洞庭湖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 “简直绝对。我在上联中用了岳飞的诗句,他就在下联中用了毛泽东的词,不仅形式工整,内涵也很深奥。” “彭公很欣赏中国的文化,他是一位很有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长者。”陈能宽说,彭桓武文化根基很深厚,不仅自己说话言简意赅、非常严谨,而且还教导年轻人向西方学习时应该有选择地学习,应该继承中国的传统。 谈起诗词,谈起中国传统文化,让陈能宽印象最深的是2005年春天他去彭桓武的新家拜访:“他搬到新房子后,邀请我去他家作客,我也一直说要去拜访他。那一次不是简单的串门,是很正式的拜访,我们整整聊了两个多钟头。”即使过去两年了,陈能宽仍对那段经历记忆犹新:“他给我讲为什么要那么对我的上联,还打开电脑给我演示他电脑里的东西,给我看他的新诗……他居然把自己的诗集全部打进了电脑,让我很佩服。” 谈到这里,陈能宽停顿了一下,声音哽咽:“没想到那是最后一次。都两年了,可我觉得时间并没有那么久,仿佛就是昨天的事情,一点一滴都历历在目。”陈能宽说,那天临走时,彭桓武还执意送他下楼,在电梯里他们还继续聊。 “彭公依依不舍,最后我说,多保重啊!他笑着说,我身体挺好的。” 谈起彭桓武,陈能宽有说不完的话,84岁的他似乎忘记了自己下午已连续开了4个多小时的会没有休息过,似乎忘了他的腿伤没有完全好。当他的助手提醒记者采访该结束时,陈能宽却拿起报纸,指着本报一篇报道彭桓武最后时日的文章说,他本来还打算去医院看彭桓武,但没有想到这么快噩耗就传来了。“能不能拜托你们记者把去看过他的人都采访一下?我们是40年的工作忘年交,我很想了解他最后的时刻,我相信很多人也都想知道。” |
附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