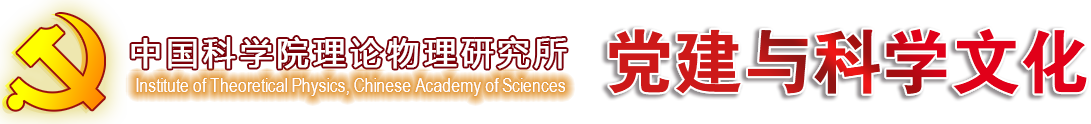央视《大家》栏目采访我所彭桓武先生
彭桓武先生---我国核工业的开拓者
马湘东:大家好!采访这些大家对我来说并不轻松,但是真正让我感到困难,甚至是有些尴尬的,还真有这么一回,那就是采访彭桓武。要知道这是一位在半个世纪前,在他还不到30岁的时候就已经名扬国际物理学界了,同时他也是我国核工业的开拓者。但是长久以来他一直拒绝媒体的采访,让我感到幸运的是,像我和他这样面对面交流的还是第一次。跟他接触让我感受最深的,还是他的人格魅力。
彭桓武的名字是和中国的核反应堆、原子弹、氢弹、核潜艇和基础物理写在一起的。他的名字前面有许多著名的头衔,但一直以来,他却把自己隐藏在普通的人群之中。
马湘东:说到两弹一星,我们知道像钱学森、邓稼先、钱三强这些科学家,但是普通的老百姓对您的名字还比较陌生,但其实呢,您恰巧是两弹一星的灵魂人物。我特别想知道您做这个无名英雄是个什么滋味?
彭桓武:不对,我也没有说做什么无名英雄,我做的事比他们做都少得多。两弹一星我只是在那儿玩了一玩,从来没有当过第一把手的那种感觉,主要的组织是钱三强,实际受苦受难比较多的大概是王淦昌。
马湘东:但是其实提到两弹一星就不得不提您的名字。
彭桓武:毕竟我年纪摆在那儿,把我放在那儿有关系。因为我原来就是原子能所的副所长,然后调过去不就是副所长就一直在那儿当领导。
马湘东:我觉得您是个非常谦虚、低调的,甚至是总是往后躲的这样的一个人。
彭桓武:就讲年龄吧,就讲在那儿的工龄吧,我很早就不做了,我现在就是在那儿什么人过生日去吃一顿饭就是了,没做什么工作。
马湘东:其实两弹一星的科学家,应该说每个科学家都有他具体的研究成果,因为这个研究成果对于科学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彭桓武:那我就是没有阻碍年轻人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没有当绊脚石就是了。
1961年,彭桓武担任二机部九部副所长,从事原子弹、氢弹的研究工作。文化大革命后我国公开参加制造原子弹、氢弹的科学家名单时,彭桓武却平静地回到了中国科学院。
马湘东:其实呢,您早在1943年,不到30岁的时候,您和另外两位科学家发表的HHP理论就已经是轰动当时的全球物理界了。
彭桓武:当时轰动一下了。
马湘东:绝对是很轰动的!那么这HHP是用您和另外两位科学家的名字的头一个字母来命名的。
彭桓武:对,“P”是我!
马湘东:“P”是您。
彭桓武:头一个“H”根本没做什么工作,挂他的名了;第二个是策划,出了个主意,不过做它,他数学不行,他这个物理想法行,数学不行,就整个的策划是他。技术、制作是我做的。这个事现在也就算历史上就轰动一下子,记载过一次以后也就完了。
马湘东:不过历史能够记载一次也就是一个不小的荣誉了。
彭桓武:历史是记载一次,还是吴有训看到那个吴副院长,他看到那个什么上头记载的说美国的科学促进会是100年还是50年我记不得了,这个时间的物理学进程。中国人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名字,我和王淦昌两个人的名字。建国以后评我们的工资就靠这个美国的这个科学促进会定的工资,所以我们都算一级享受了。
马湘东:应该说他是位天才,我就特别想知道说这位天才也称您为天才……
彭桓武;这我知道什么道理。因为他做一个什么东西,我给他出了个点子,也是数学上的诺特定理,他大概对这个不怎么熟悉。我这些个数学方面都是马克思波恩,他的老师传承下来的。我在马克思波恩那儿,他有一个私人的图书柜子,我可以随便看,虽然是德文的,我可以随便拿出来看,他允许我去看他的书,所以我在那里学那些个叫做德国的格廷根学派,那是数学老祖宗,几代都是数学名师在那儿,所以我的数学在那儿学得比较高深。
彭桓武的博学多才是与他勤奋读书、埋头研究分不开的,被同事们称为半个化学家的彭桓武,在他57岁的时候,开始学习令许多数学家都望而生畏的拓扑学。他的治学和为人之道影响了整整一代理论物理学家。在他的人生历程中,惟独让他看重的只有一个头衔——中国物理学家。
马湘东:我也听说小时候您的私属老师说,此童未学做赋却已能做赋,就是说你还没学会做诗就已经学会写诗了,怎么会这么神奇呢?
彭桓武:这属于模仿,文学方面是模仿,就是照抄人家的东西,模仿。
马湘东:您觉得自学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彭桓武:不知道,我这个自学反正是从小在家里念过一套,看过一套《史记》这也是完全自学,后来在清华二年级暑假看《先秦诸子》那些个东西也是自学,自学看书,把老古董的书拿来看就是。
马湘东:您看这个您这么喜欢文学,自己做诗,但是后来又学了物理。
彭桓武:我这些个东西都是没有上初中以前,我念《史记》,念中国文学都是没上初中以前的。
马湘东:那中学什么样的?
彭桓武:中学一下子讲几何,讲物理,我马上就读遍了,就完全就学这套了。
马湘东:您觉得几何也好,物理也好,什么东西特别吸引您?
彭桓武:比中国那一套老东西还是吸引人,我马上就变了。
马湘东:您能谈谈老师的这种启发式教育对您的影响吗?
彭桓武:像物理的那个问题的公式,那时候以为公式都是总结实验经验来的,结果有一个公式太复杂了,我想不出怎么能够实验出来会凑这么一个复杂的公式我就拿去问他了,他是北大毕业的,拿了一本北大,他们念的大学物理第一年级英文的教科书。那时候都是找出一个图纸这里有解释,我就把这个书借过来,看了,答应三天以后还他。这样我不但把它看懂了,英文也过关了,英文教科书可以看了,问题也解决了,他并没费任何力气,就是指了一个图,然后把书借给我,这样的老师我认为是最好的。
马湘东:您刚才说的可能因为是老师教得好,再加上您非常有兴趣,所以您其实16的时候就已经进了清华大学了,等于跳过高中了。
彭桓武:高中基本上念了半年的野鸡中学,拿了一个文凭了。
进入清华大学,彭桓武严格遵循着他的主修物理、选修化学、旁听数学的学习计划。每一天他都是在紧张而又有序中度过的。清华六年,他和王竹溪、林家翘、杨振宁被称为“清华四杰”。1938年他考取庚子赔款惟一理论物理研究生的名额,踏上开往英国的轮船。
马湘东:但我觉得有一件事您特有意思,就是在我们采访之前,我们聊天的时候您在看那个王淦昌的书。然后您自言自语说下面这段我不看了,我问您为什么不看呢,您说因为我这一看到他的遭遇或者让人伤心的地方就不看了。
彭桓武:对!我想当年我看《三国演义》也是,诸葛亮死了以后我就不看了。
马湘东:您这个挺有意思的,一到坏的或者悲伤的您就不看了。
彭桓武:对,我就不看了,看起来挺难受的,干吗要去看呢?不热闹了也觉得。
马湘东:那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您?是因为您乐观的个性呢,还是您对这些东西去逃避它或者去躲避它呀?
彭桓武:不知道,反正没有道理。你比如说社会新闻我很少看。
马湘东:为什么?
彭桓武:讲些什么没道理的事,这个那个的,坏事看起来使人生气,该杀该打的那些人
那看着有什么意思?我又不会向他学习!
马湘东:您是不是平时也是个比较乐观的人?
彭桓武:你说一点悲观情绪没有大概不会的,你看我的书就知道了我带着药到上海,让我姐姐给收掉了,砒霜!那就是悲观了,因为我不会对付他们,要日本人要拦住我,怕问什么
我一定出了问题,活不下来……
马湘东:那这确实挺让我吃惊的,没有想到在那个年代你会有想吃砒霜想自杀这样的念头。所以可能后来不去看一些书,有些时候不去看一些悲观的东西,是不是怕揭开这个伤疤?
彭桓武:不知道!不懂!
马湘东:彭老,您有没有对自己反思过,这样的唯物也好,这样下去读三代以后的书会不会有些偏激呢?
彭桓武:当然是偏激了,我所以说就偏激得很厉害。我把这整个的礼教都偏激了,跟人不接触了,都偏激掉了,现在的话叫做什么——澡盆子扔了,把里头小孩都给扔了这句话,我不知道那个话怎么说,就是那个意思,我就是这样,所以当然偏激了,所以我公关是不行了。
马湘东:但是这种偏激用在科学上刚好是一种执著!
彭桓武:也就是只能干这个事,不是执著,别的都不行,也就只好干这个了。
马湘东:那么您对科学家和领导者这两个角色是怎么定位的?
彭桓武:我对领导者的角色我不敢当。我就做了一任所长何祚庥副所长全权代理,完了,我什么也不管了。我根本不称职,我去做所长我怎么会做?
马湘东:我跟您的谈话当中感觉到您的这种淡泊名利,非常超然的一种个性。
彭桓武:也不是淡泊名利,就是那些事我根本不称职。你说什么当政协人大代表,我自己
三届人大代表,一届政协委员,从未提过案,从未发过言,理应革职,我自己就给自己革职了,根本不称职你去做那个干吗?
彭桓武43岁结婚,老伴去世,惟一的儿子也远赴美国求学。76岁他学会了做饭,几十年来,彭桓武独自一人过着简朴的生活。80岁的时候,他以自己独有的方式设立了一个特殊的奖项。
马湘东:您在95年的时候获得了何梁何利奖的“科学与技术成就奖”,那么当时这个奖金是一百万港币,我想可能也是您一生中获得最高的一次奖金了。
彭桓武:对!这一百万港币到明年就完全报销了,到明年就结束了。
马湘东:因为您把它全部捐赠了。
彭桓武:全部赠了,纪念赠款就完结,明年就结束了。本来应该是明年和后年,不过我现在这个身体状况,我想把后年的提前就明年一块儿,两届一块给掉算了。
马湘东:您设立了彭桓武纪念奖,我关心的是这一百万对普通人来说,他可以过着一个舒适的生活,但这一百万对您来说……
彭桓武:对我说没用,我生活足够了,加这一百万不加这一百万,这一百万等于白搭。因为你一个人只能用那么多钱,你像我现在吃,大夫给我限制的,我只许吃这么多东西,一天只许吃一个鸡蛋,吃两个鸡蛋都不行,那个钱有什么用?
马湘东:彭老,这一百万我注意到现在已经有将近35个科学家获得了这笔奖学金,分到他们每个科学家的手里呢也就剩下了三万人民币。
彭桓武:三万块钱。
马湘东:那么这三万块钱,您想通过它来表达您对这些科学家的一个什么敬意呢?或者说您觉得三万块钱,对他们来说能解决生活的实际困难吗?
彭桓武:没那个意思,就是表示纪念而已。就是纪念当初合作过、工作过就完了,就是个纪念的形式,这钱的多少没有什么用处,那个没有,那三万块钱算什么呢。
马湘东:彭老,您的老伴儿75年就去世了,到现在已经30年了……
彭桓武:77年!
马湘东:77年去世了,到现在已经快30年了,一个人,您一个人做菜、洗衣服,五年、十年我们能理解,但一个人30年这样……
彭桓武:那都有人帮我忙,有人帮忙,我一共做了十年的饭。
马湘东:这些年你不觉得孤独吗?
彭桓武:不孤独,我有物理,理论物理陪伴我,不孤独!
马湘东:那是不是说在您倔强的外表下。其实……
彭桓武:升华过去,就是升华,要实在难受就写诗,所以我那诗里就有三分之一是写我老伴儿。
马湘东:您刚才谈到升华,难受的时候您就写诗,它是怎么样的一种升华?
彭桓武:就转移注意力,这是心理学的措施,转移注意力,干事去就完了,就没功夫去想这些废话了。
马湘东:那您为国家做了这么多,您留给自己的是什么呢?
彭桓武:留给自己的就是乐趣呀,做事的乐趣!
马湘东:这么多年您是一个人过,然后在这样的环境里,大家其实最后终究想知道的还是您在追求什么?
彭桓武:追求什么?科学家的追求还是做工作,这很清楚嘛!王淦昌临死以前我见他最后一面,他就说,“我能做的都做了,再有工作我也做不了。”就是这样,就是要做工作,科学家最高的追求也无非就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