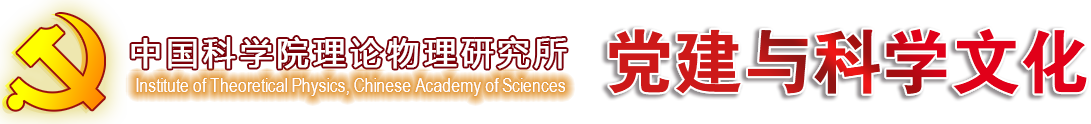我的导师于敏先生- 赵恩广
我在1963年考上了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的研究生,导师是于敏先生。那时,我国还没有学位制度,因此也没有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差别。唯一的差别是,一般高校的研究生是三年制,科学院的研究生为四年制。所以,我应当在于先生的指导下,学习四年。后来,由于参加“四清”和“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我的研究生学习时间,只有两年。但是,这两年里从于先生学到的东西,一直影响着我四十多年的科研生涯。
我记得,在我第一次到原子能所的中关村分部报到时,管研究生的同志给在原子能所本部的于先生打电话,询问把我放在分部还是放在本部。于先生的答复是,放在中关村分部。后来,我才理解于先生这一决定对我后来所走的道路的重要影响。
当时,于先生还有一位来自清华大学的研究生吴慧芳。在学习的第一阶段,于先生布置给我们的习任务是,读Rose的“角动量理论”一书。当时,我对这一布置,并不太理解。但也只好硬着头皮去学习。只是在以后的研究工作中,我才逐渐体会到角动量理论的重要性。这本书的很多内容,不断地应用在我的研究工作中。在第二阶段的学习任务是,仔细阅读夏蓉的“原子核理论讲义”一书。这是当时唯一的一本中文的原子核理论书籍,是根据杨立铭先生和于敏先生在成都的暑期学校的讲稿,编写成书的。现在,这本书已经无法在书店找到了。但是,它仍然是我们这一代人经常翻阅的主要参考书之一。它对我国的原子核物理的发展,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进入学习的第三个阶段后,我们的主要任务是,阅读有关核超导的文献。这些文献,大都收集在“物理译丛”的1964年第五期上。主要的文章有,A. Bohr, B.R.Mottelson and D.Pines的“核与超导金属态的激发谱间的可能相似性”,B.R.Mottelson 的“原子核结构”,L.S.Kisslinger, R.A.Sorenson的“单闭合壳层核的对偶力和长程力”,S.T.Beliaev 的“正则变换法在原子核中的应用”以及 M.Baranger 的“重球形核壳层模型的推广”等。这些文章,至今仍然是核超导的经典文献。这三个阶段学习结束时,两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在我们的学习期间,于先生不断给我们布置作业,还认真批改我们的作业。这样做,恐怕在研究生培养中,并不多见。而当我后来指导我的研究生时才发现,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从1963到1965的两年间,他几乎每周接见我们一次,先是让我们汇报学习情况,特别强调要我们向他提问题。我们问得多,他就很高兴,并很热情地解答;如果我们没有问题,他常常怀疑我们是不是真的把看过的东西弄懂了;有时,甚至要批评我们。那时,每次接见前,我们都要绞尽脑汁地从看过的文章或书籍中寻找问题。后来,我逐渐体会到,通过找问题,确实可以加深阅读的效果。更重要的是,它培养了我的一个习惯,喜欢换一个角度来看同一个问题。这样做,常常会使我在研究工作中,产生新的想法。
于先生一次问我们,什么是热中子,它的能量是多少,这个能量是怎样得到的。当时,我们没有答出来。他就让我们回去考虑。于先生还经常提醒我们,应当记住几个常用的物理常数的数值,如普朗克常数,玻尔兹曼常数,电子电荷…等等。这样,就可以很快地对很多问题进行定性估算。他非常强调定性估算的重要性。在80年代初期,理论物理所成立不久,一次和彭桓武先生聊天,我讲起于先生对我们的这个要求时,他很赞同。并且马上问我,你说说,1 MeV 相当于绝对温度的多少度?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当时原子能所一分部的一些年轻人,其中也有我,一起去访问于先生,就一分部的科研发展方向,征求他的意见。他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相当坦率地谈了看法。在一张纸上画了一个圆圈后,他对我们说,这个圈内是原子核物理,我们已经对圈内有了很多的认识;当然,圈内还有不少东西至今仍然不清楚。不过,核物理超出这个圈的可能性不大了。因此,我们今天可以给核物理画这个圈。但是,对高能物理,我们还不能画这个圈,我们不知道这个圈有多大。因此,他建议我们要多关注高能物理。于先生的这个看法,可以说是建议原子能所一分部转向高能物理的最早建议之一。同去的几个人,现在大都在高能物理所工作。遗憾的是,我并没有听取于先生的建议,而是一直固守在原子核物理中。不过,于先生这个画圈的思考方式,却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以后,每当我考察一个新领域时,我也经常要想一想,能不能画这个圈。如果人们已经画了这个圈,我们能突破它吗?
进入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我和师妹赵维勤经常在春节时去看望于先生。他和师母每次见到我们,都非常高兴,很热情地招待,使我们感到非常的亲切。在轻松的聊天中,得到很多的支持与鼓舞。一次,我谈起在研究生学习期间的收获时,他却很谦虚的说,很遗憾,在你们的学习期间,没能指导你们做一个完整的研究工作。这当然也是我们的遗憾。由于文革,从1966年的夏天起,我们的研究生学习中断了,再也不能恢复了。但是,跟于先生学习的这两年中的收获,却使我受益终生。我们从于先生那里学到的,不只是学业与科研的方法; 更重要的是,还有做人的基本原则。
记得文革结束后不久,有一次去家里看望于先生。我问他,“文革中的大字报上说,你欣赏诸葛亮的一句话“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有这回事吗?” 他反问我,“淡泊一点,宁静一点,有什么不好吗?”是的,这没有什么不好。孔明先生的这句话,千百年来成为很多仁人志士的座右铭,在淡泊与宁静中,书写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我的导师于敏先生,也是这样,在淡泊中凝练着自己的坚定志向,在宁静中辛勤而执着地为祖国的核科学事业无私地奉献着。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 赵恩广
2006年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