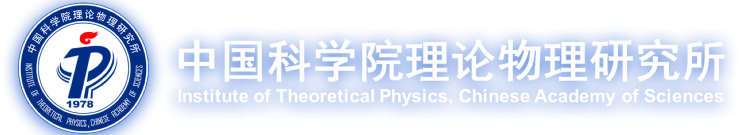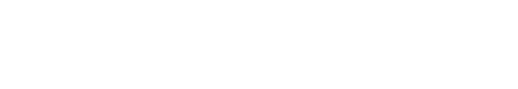邹冰松:为而不争

邹冰松

邹冰松(右)在国际会议上担任主持人。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吴佳俊一直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见邹冰松时的场景。那是大三暑假,吴佳俊来到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高能所)跟随邹冰松做“大学生研究计划”,走到高能所大门口,给邹冰松打了电话。
“那时周边还是土路,邹老师担心我找不到地方,便让我在门口等着。大约几分钟后,看到他身穿白色短袖衬衫、米黄色短裤,推着一辆黑色二八自行车走了过来,笑着向我打招呼,然后帮我把行李放在后座上,带我去住宿点、办公室。”
如今16年过去了,吴佳俊已是中国科学院大学助理教授。邹冰松则因在强子物理领域的杰出成就,于2021年11月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吴佳俊心里,“邹老师外表儒雅温和,内心却十分坚定”。
目标明确,从不“广撒网”
当选院士后,更多的邀约纷至沓来,邹冰松的手机、办公室“热闹”了起来。“除了与我研究相关的,能拒绝就拒绝。”邹冰松说,“院士”也不是什么都懂。
如今,喧嚣渐散,邹冰松再次走回他的理论物理世界,在办公室里以思考、交流为乐。他的生活照旧,每天在家吃过早饭,9点到办公室,晚上10点左右离开。午餐和晚餐在园区食堂解决,一荤一素一碗免费汤。
“我想干什么?对方需要什么?我能做什么?”邹冰松是个目标非常明确的人,这样的思考贯穿于他每一次选择中,让他在理论、实验和计算交叉的物理学领域不断作出开拓性和突破性成果。
1980年,邹冰松考入北京大学。他喜欢核物理,当时这是“冷门”专业,亲友因误解其“有辐射、危险”还曾“劝退”他,但他依然坚定地选择了这个专业。
申请博士后时,因想做介子相关理论研究,邹冰松只给美国、加拿大和瑞士的国际三大“介子工厂”投递了简历。与稳定的电子、质子相比,不稳定的介子实验更难做,三大“介子工厂”在介子研究方面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我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想做什么,便联系相应职位,而不是‘广撒网’,这样能让对方更好地了解你,知道你是有准备的。”邹冰松告诉《中国科学报》。
1990年,26岁的邹冰松申请到瑞士国立粒子和核物理研究所(又称保罗谢勒研究所,PSI)博士后职位,成为国内第一个申请到PSI理论室正式博士后的学者。
回国亦是如此。上世纪90年代末,北京谱仪运行近10年,积攒的强子谱相关数据量几乎与国际相当。然而,高能所科研人员却向邹冰松表达了担忧,“分析水平不行,强子谱方面难以出成果,数据也可能会废掉,你能回来吗?”
1998年,邹冰松决定回国,选择了高能所。他十分清楚自己的优势和目标:与高能所理论物理研究室的粒子场论组、核物理组均有合作;鉴于国外的工作基础,他自信能够帮助提高北京谱仪的实验数据分析水平。
入职后,邹冰松迅速组建课题组,提供理论公式和程序,培养物理分析人才,推行先进的全信息协变张量分波分析法,获得了大批基于谱仪的物理成果产出,使北京谱仪的强子谱物理分析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
强子谱分析让邹冰松初露头角,随后他在国际上率先提出利用衰变开展核子激发态和超子激发态重子谱研究,与北京谱仪实验组的同事发现了3个新核子激发态。
那时,中国重子谱研究几乎不为人所知。2000年,美国杰弗逊国家实验室组织召开国际会议,邹冰松带着最新研究成果报名参加。他作完报告,几位美国教授立马找到他,惊叹“没想到在中国能做这样的研究”。
邹冰松所开创的重子谱研究新项目,使我国在重子谱这一国际物质微观结构研究的前沿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
一片充满冒险的广阔天地
很多公开场合介绍邹冰松时称他为“理论物理学家”,但他更愿意把自己看作是理论与实验的“桥梁”。
前往PSI之前,邹冰松原本想继续博士生时从事的理论物理研究。然而,到PSI不久,他找到了更喜欢的研究。
PSI坐落在阿尔卑斯山脚下,毗邻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它拥有目前世界上最高能量的大强子对撞机等全系列的粒子加速器系统。在这里,邹冰松第一次感受到来自粒子物理实验与理论互为协作的冲击。
邹冰松的博士后导师同时也是苏黎世大学教授,他们与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新兴低能反质子实验开展合作,经常组织讨论会,邹冰松主动参与。“新兴实验毕竟没有长时间积累,有一定的冒险性,但肯定会出新东西。”理论与实验密切结合,成了邹冰松的新兴趣,一直坚持至今。
找到热爱的方向,并乐此不疲,邹冰松也时常这样教育学生。邹冰松从不“push”学生,大多时候教导他们要对科学有兴趣,因为只有内在驱动才会更加积极主动,“只有自己想做,才会有更好的发展”。
两年后,“为了与实验联系更密切”,邹冰松申请到了英国伦敦大学QMC—卢瑟福实验室研究助理职位。在这里,他加入了欧洲核子研究中心低能反核子实验国际合作组,负责做实验数据的理论分析。
邹冰松与合作者采用符合实验数据的新处理方法,重新分析了低能反质子相关实验的数据,推翻了6个国际合作组过去的分析结果,根本性改写了原来的轻标量介子谱。
“对实验不了解,或对相关理论缺乏了解,做出的数据分析结果常会出错,因此,理论与实验结合非常重要,这方面人才也非常缺乏。”邹冰松看到了这片广阔天地,并试图填平两者之间的“沟壑”。
作为一名理论物理学家,邹冰松认为,“超前的原创理论必不可少。思考实验当下做不了的原创思想,需要好奇心驱动的自由探索”。
不过,这类研究更难。邹冰松最有影响力的发现之一就是,提出了超出经典夸克模型的重子五夸克成分新见解,预言了一类隐含重味的五夸克态,并于2015年至2019年被LHCb实验观测确证。这项研究他花费了近10年的时间。
吴佳俊参与了这项工作。他回想起投稿经历时告诉《中国科学报》,一开始,他们把这一成果投给物理学顶尖杂志《物理评论快报》,被拒绝发表。一条评审意见是“太早了,距离能做实验还需5年” 。
“理论就应该走在实验前面。”他们说服了杂志编辑,最终得以发表。“我国在强子物理领域已经走到了世界前沿,邹老师带领的团队是最重要的力量之一。”
在邹冰松看来,理论物理研究一定要有好奇心驱动的自由探索。诺贝尔奖大多颁给提出原创思想的人,比如“上帝粒子”黑格斯粒子的发现。“思考一些实验当下做不了的东西,允许一小部分人自由探索,支持一批有梦想的人做最原创的研究。”
驱动力不是“push”来的
邹冰松的学生群里流传着一张照片——凌晨1点,清冷的道路上只有邹冰松一人,昏黄的路灯映衬着他回家的背影。
“邹老师特别勤奋,晚上8点以后去找他,他基本都在。”吴佳俊说。那时,邹冰松已担任理论物理所副所长,白天忙行政事务,晚上继续做研究。
在邹冰松看来,热爱便不觉得累,“如果你真的对科学感兴趣,没有条件也会创造条件”。其实,这种“吃苦”精神在他儿时就得以锻炼。邹冰松不疾不徐,崇尚“为而不争,上善若水”。
“绅士、儒雅”,提起对邹冰松的印象,理论物理所的人脱口而出。这几乎也是所有人第一次见到邹冰松的感觉。在吴佳俊的印象中,邹老师从未跟学生们红过脸,“‘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没完成’可能是他说的最严厉的话”。
吴佳俊记得,只要邹老师在所里,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去找他。不过,邹冰松的要求高于博士生毕业标准,“他会早早地给学生定下培养计划,指明方向,布置课题。这种培养方式激发了学生们的主观能动性”。
邹冰松的3个孩子全都考入了北京大学,但对待孩子,他也从不“push”,充分尊重他们的兴趣选择。有时面对孩子似乎有些“不上进”的提问,邹冰松觉得“没问题”,是金子总会发光。
他与从事生物类研究的夫人从未打骂过孩子,从小培养他们的独立意识。他们没有专门费心让孩子上更好的重点小学,而是选择就近上别人眼中比较一般的学校;送孩子上托管班,自由选择兴趣小组;从不督促写作业,不安排放学之后的补课;大学选什么专业、留学上哪个学校,全程由孩子自己操办……
“我们家基本上是晚上10点后才聚齐,白天都各忙各的。”作为一名科研人员、课题组长,邹冰松平时有繁忙的科研工作,但接送孩子、开家长会、与老师的交流沟通几乎都不缺席。
如今,3个孩子中只有一个学自然科学。“他学了生物物理学,我们现在就指望老三成为科学家,希望能超越我们俩。”邹冰松笑着说。